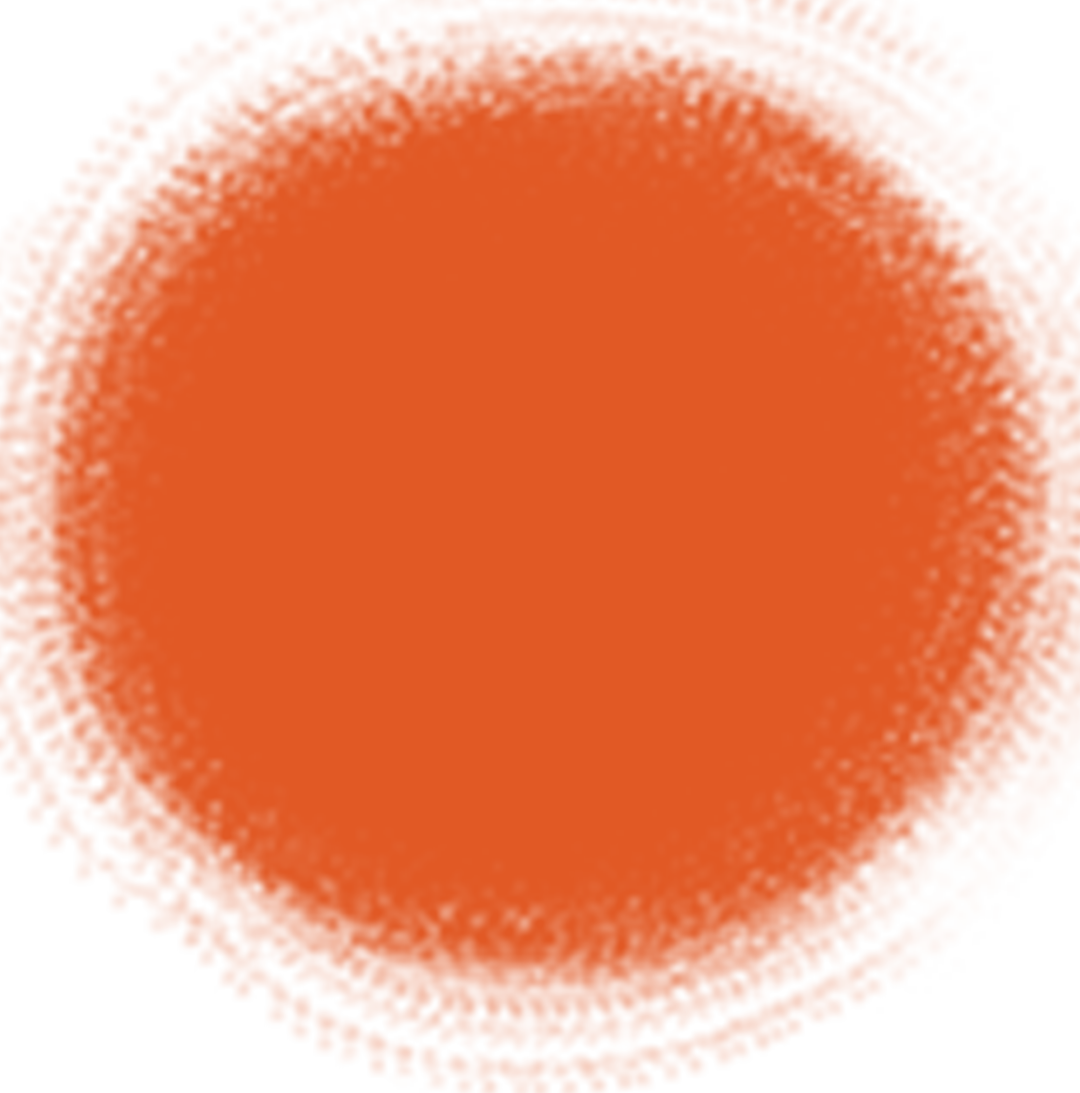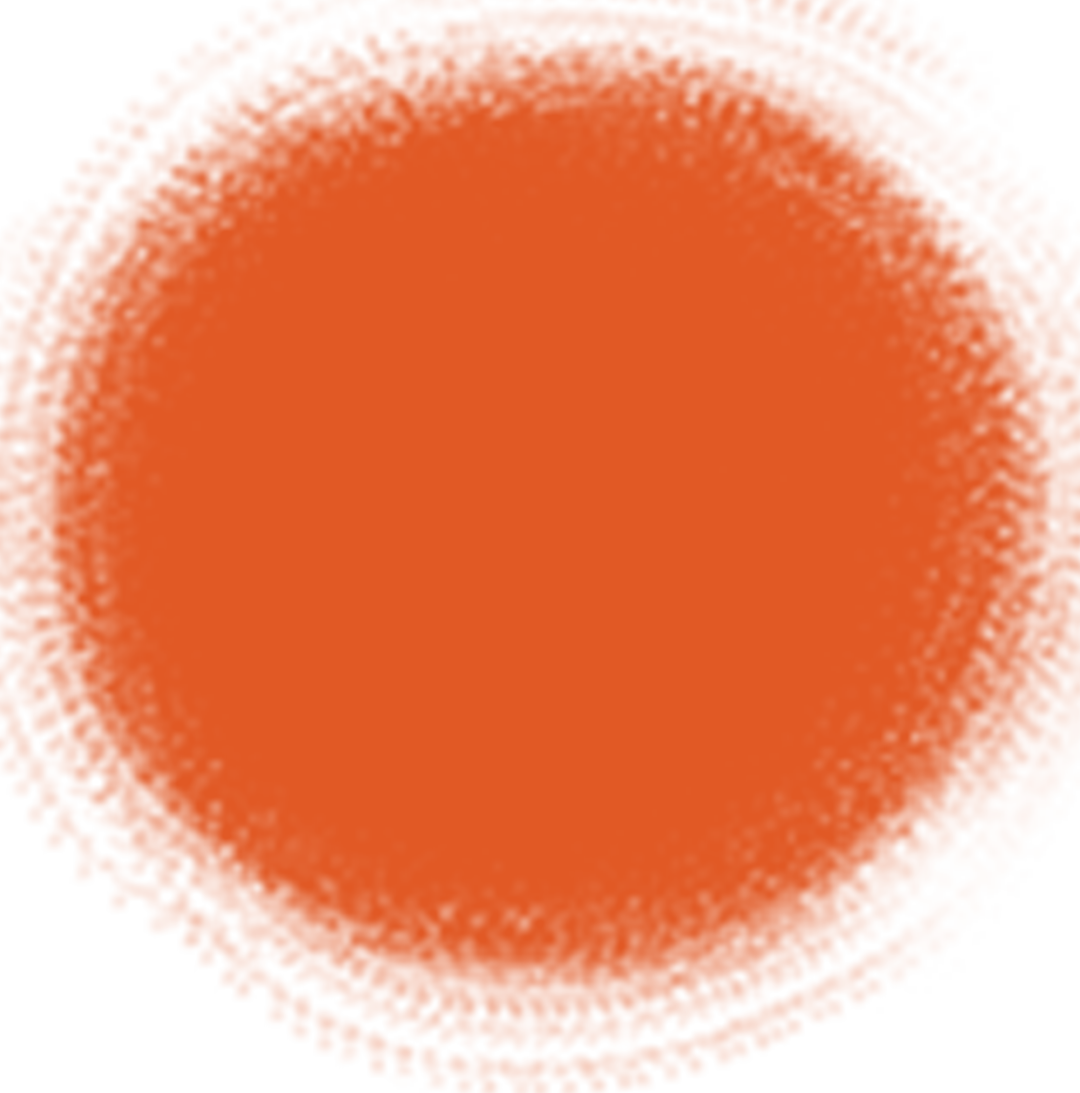

扬
戈
五谷六畜最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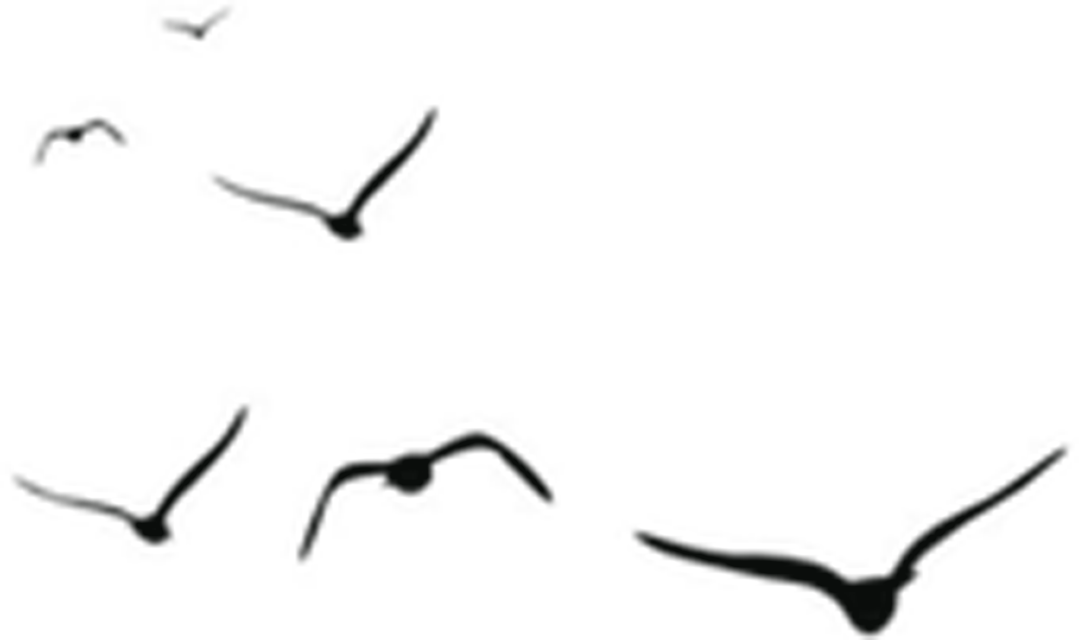
在第一节中,我们讲述了采集农业向原始农耕和畜牧业过渡。经过先民们长期耕作经验积累,最终筛选出了适宜人类饮食需求的“五谷”和“六畜”。小时候过年,家家户户都贴春联。大门上横批喜欢贴“五谷丰登”,猪圈、牛圈则贴上“六畜兴旺”。寄托着民户对来年粮食丰收,以及家畜兴旺的美好愿望。
“五谷”之说,在中国出现特别早。传说神农时期,天降粟米,神农开始种植推广,逐渐取代了采集农业[1]。还有传说,周人的老祖宗后稷,教授民众农业,种植五谷,解决温饱问题[2]。但不管怎么说,毋庸置疑的是,五谷在中国起源很早。
关于“五谷”的说法,版本很多,流传最广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黍、稷、麦、菽、稻;另一种指黍、稷、麦、菽、麻,两种说法的区别在于有无稻、麻。黍、稷,就是小黄米,现在基本上不再种植;菽是大豆,就是打豆浆的豆子;麻是古人做衣服的原料,它的果实叫麻子,可以直接嗑食,相当于瓜子般的零食。以上这四种作物到秦汉时,由于产量不高,其重要性逐渐减退。而小麦和水稻产量高,因为食用性强,逐渐成为主要农作物。
现在,大多数人都住在城镇,脱离了农村,几乎都不认识农作物,闹过很多笑话。我上学那会儿,陕师大长安校区对面还是农田,尚未开发成房地产。我有一个陕北同学,看到一大片麦苗后说:“好大的一片韭菜,这能包多少饺子呀!”当场我就石化了。陕北地区很少种小麦,主要种植土豆、小米(粟)、玉米等农作物。我同学没见过小麦,所以闹了笑话。
这让我想起《论语》中的一个典故:孔子爱徒子路,也遭到过农民伯伯的鄙视。孔子带弟子周游列国,子路一不留神给走丢了,迷路了。于是,他就向路边的农民伯伯打听,您看到我老师了吗?老农看着他,调侃地说道:“你这样的人,既不参加劳动,又无生产常识,谁敢当你的老师?”[3]关于这段话,还有另外一种理解:“我忙的手脚不闲,五谷都来不及种,哪有闲功夫管你老师是谁?”笔者更赞同这种说法。
未被列入五谷的粟和高粱,反而是古人主要粮食。因为南北气候差异,中国还形成了“南稻北粟”的种植格局。粟,就是小米。汉初文帝时,“入粟拜爵”,政府公开售卖爵位,或者赎买罪刑,计价单位就是粟[4]。古诗文中有不少都涉及到粟的:比如说杜甫在《忆昔二首》中讲:“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朱子家训》中劝诫子孙珍惜粮食:“一粟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应念物力维艰”。
高粱,是原产于非洲的古老农作物。中国人种植食用高粱其实很晚,高粱大致上是在两汉魏晋及宋元时期通过多种渠道先后传入中国的[4]。以前有学者说,高粱在史前时期就传入中国,这个说法可能站不住脚。我们只看两点:一是考古发掘的古墓葬遗址中,在宋以前没有出土过高粱的;二是宋以前的各种诗文典籍中,也没有看到过高粱的记载。
再查现存农书,最早记载高粱种植方法的是元代的《农桑辑要》。这本书的参考书目叫《务本新书》,而《务本新书》是金代学者的著作。据此可知,有人将《论语·述而》中的“饭疏食饮水”解释为:吃粗饭喝清水,这个粗饭就是高粱饭,纯属胡扯!同样,颜回由于家贫,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依然能够安贫乐道,坚守志向,获得孔子点赞[6]。颜回食用的粗粮,应该是黍、稷,或者是粟,而非高粱饭。
小麦,原产西亚两河流域,商周时期传入中国,春秋时代逐步推广。这在《诗经》当中有所体现,《诗经》中讲:“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意思是说:上天赐予我们麦子,天命用它来供养。不分彼此和疆界,遍及中国都推广。熟悉近代史的人都知道,轮船招商局会办朱其昂在天津开办一家面粉厂——“贻来牟”机器磨坊,使用的就是《诗经》的典故。
小麦推广种植极为缓慢。到西汉武帝时期,小麦仍未普遍种植。麦子虽然也是旱地作物,却比粟、黍的灌溉条件要高。此外,当时面粉加工业落后,尚未掌握磨面技术,麦子无法去皮磨碎,变成精粉。只能煮麦粒吃,叫“麦饭”,与粟、黍相比,口感极差。政府征税都不收麦子,农户只有留下自己吃。官员若吃麦饭,则被视为清廉,子女在守孝期间吃麦饭,则是遵从孝道的表现。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磨面技术才逐渐成熟,小麦逐渐成为国人主食。
汉武帝对外征伐,粮食消耗巨大。为弥补粮食缺口,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麦饭虽然难以下咽,但因其产量高,可以在关中广泛种植小麦,不要错过种植节令[7]。汉成帝时,著名农学家氾胜之担任“劝农使者”和“轻车使者”,指导农业生产,在长安附近推广种植小麦,小麦获得大丰收[8]。此后,小麦种植快速向黄河中下游推广,并出现了粟、麦轮作制。
西汉政府推广种植小麦,除了战争环境,还与气候突然转冷有关。武帝以前,北方气候温湿,关中竹林广布,班固称其为“陆海”。当时关中广泛种植水稻,《氾胜之书》中还专篇介绍水稻种植方法。武帝以后,进入小冰期,气候骤然转冷。尤其是两汉之际,极端天气连绵不断,农作物甚至颗粒无收。进入东汉,气候更为寒冷,水稻种植从黄河流域南移到温暖湿润的长江流域,寒性更高的小麦在关中地区推广开来。
五谷讲完,我们说六畜。“六畜”包括猪、牛、羊、马、鸡、狗等六种禽兽。人类发展史的分水岭,便是由食物的采集者(采集经济和荒野猎人)演进为食物的生产者(原始农业),由被动获取变为主动种植。种植谷物,驯养动物。“拘兽以为畜”[9],人们将打猎捕获到的禽兽圈养起来,就出现了早期畜牧业。春秋战国时期畜牧业走向繁荣。比如说春秋晚期猗顿[10]、战国时期的乌氏倮[11],都是因畜牧业发家致富,甚至位列朝堂。
六畜,分为“食用型”的猪羊鸡,“动力型”的牛马。当然,按照国人无所不吃的性格,必要时,狗也是一道菜。甚至还出现了杀狗职业,比如汉初大将樊哙,就是“屠狗”出身的,杀狗专业户[12]。这些温顺的禽兽,饲养的时候叫畜,屠宰的时候叫牲,合起来就叫“畜牲”。
古人祭祀用六畜,其中色纯的叫“牺”,体全的叫“牲”,合在一起就叫“牺牲”。古人敬重祖先、神祗,请他们吃饭,自然要拿出最好的,六畜成为不二之选。中原不产马,狗肉不上席,鸡肉太小气,只好“牺牲”猪、牛、羊这“三牲”了。能够成为祭祀贡品,算是它们“三牲有幸”,呵呵。
猪,在中国曾被评为“最有影响力的家畜”。猪的重要性,从很多农谚中就能体现出来:“六畜兴旺猪为首”、“种田不养猪,十年有九输”、“扫盲要读书,增产要养猪”等等。猪存在意义在于:一是献出自己的肉体,任人宰割,让人吃掉。舍得一身剐,敢把大家吃胖傻!二是展现生理缺陷,让人辱骂。它是懒惰(懒得和猪一样、比猪还懒)、蠢笨(蠢猪、笨猪、死猪笨)、好色(咸猪手、猪哥)的代名词。
牛,传统农业社会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在“耕牛”出现之前,先民的翻地工具叫耒耜。“耒”起初就是一根尖头木棒,类似一根短柄标枪;改良后叫双齿耒,状似“Y”形的木叉。韩非说:“大禹作为天下共主,公仆精神十足,心系人民,亲执耒臿挖土,奔波在田间地头,带领人民致富奔小康。起早贪黑,非常异常。”[13]汉人梁武在《石室画相》中,绘制了个“神气活现”的农民——神农,他手中抓着一柄状似铁锹的农具,就是再升级版的耒锸——在耒的歧头上安上以横木,便于踏脚,节省力气。
“耜”,其形若耒,区别在于“耒下歧头,耜下一刃”,耒分岔两头,耜扁头一体[14]。木柄前端安装上矩形石片,或者宽大骨片,就是一个简单的耜,类似于今天使用的铁锹。张荫麟先生指出:“耜和耒的分别是下端斜锐而不分歧,利于刺地而不起土,大约过于坚实的土,耒不能起便先用耜去刺松。”[15]耒耜的终极版本,就后世翻地所用的犁。“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耒耜看似简单,在传统农耕时代,却应该获得“农业科技进步一等奖”。
与耒耜配套的耕作方式是“刀耕火种”。焚烧草木,疏松土质,变废为宝,翻土耕种,草木灰可以提升土壤肥力。传统农业讲求:“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原始先民尚不懂使用粪肥。不给土地追加粪肥,土壤肥力容易耗尽。因此,疯狂的原始人经常迁徙,开荒种地。这可能是“商人屡迁”在经济上的反映。刀耕火种,肥力耗尽,只能另谋出路。
从春秋战国开始,铁犁牛耕的出现并得以推广,发生了农业生产力革命。西周时,用耒耜耕种,“一人跖(踏)耒而耕,不过十亩”,一个人用脚踏耒翻地,一天最多只能翻十亩。而到战国时期,用牛耕地,五口之家,一天耕种上百亩(相当于现在的31亩),每亩收1.5石,总共收150石[16]。牛耕不但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提高了耕种效率,还可以深耕,有利于提高粮食产量。所以,古代政府严格保护耕牛,谁敢公开杀牛,会被政府杀头“弃市”。牛命比人命金贵多了!
而很多“脑残型”古装影视剧中,大侠下馆子的标准套餐:“小二,来十斤熟牛肉,再来一坛上好女儿红。”(难道就没有别的酒菜吗)大侠就是大侠,只吃牛肉,不怕被杀头弃市。古人想吃口牛肉不容易,和现在去饭店点个“红烧大熊猫”差不多!牛在古代中国的地位,堪比今天牛在印度,可以横行无忌。牛之于中国人的重要意义,熊培云先生给了恰如其分的解说:“与其说我们是‘龙的传人’,还不如说是‘牛的传人’”[17]。
马,比其他动物出现的要晚(大约5000年前)。但因为其速度更快,力量更强而后来居上,成为古代军事活动、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的重要工具。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马属于哺乳动物奇蹄目,每个脚长五个脚趾,后来除了第三趾,其余四个脚趾全部蜕化掉了,只剩下一个脚趾,这样的身体结构有利于快速奔跑。马是奔跑最快的动物之一,最快时速可达60多公里,并且可以连续奔跑上百公里,所以有“路遥知马力”之说。
马是动物中的“贵族”,不像其他动物卧倒休息,它是站着睡觉的。若一匹马躺倒时,便预示着它的“末日”即将来临。马的智商很高,一匹成年马的智商相当于5岁孩子的智商。马外表安静温顺,但骨子里却桀骜不驯,尤其是哪种“千里马”,更是很难驯服,骑手必须在体力上和智力上都获得它的认可。一旦认主,则生死追随,不离不弃。古今中外,这样的事例多不胜数。所以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说。
马被用于军事,起初是拉战车。直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从匈奴那儿学会骑马(当时匈奴无法制造精良战车,便发展了骑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才跨上了马背时代。而秦赵长平之战,便是战国时期发挥骑兵“兵贵神速”的经典案例。秦国以5000骑兵迅速绕过赵军侧翼,斩断其粮道,分割包围赵军,最后坑杀赵国精锐的。
战国时代,骑兵并非马上厮杀,马更多的是充当运输功能,骑兵骑着马冲到跟前,然后翻身下来,拎着武器上阵杀敌,所以“马到成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汉代,直到马镫的发明,才解决马上打仗的难题。马镫这个看似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发明,却姗姗来迟。有了马镫,骑兵在马上才使得上劲儿,射箭、劈刺的功效大为提高。
大家是否发现,秦始皇兵马俑,汉阳陵的马,马身上都没有马镫,绝大多数也没有马鞍。汉以后马镫出现,人马合一,马上白刃战,骑兵成为冷兵刃时代的霸主。汉武帝时,骑兵一度达到巅峰状态,拥有甲兵45万,军马60万匹。这也是为什么汉代敢口出狂言:“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匈奴被两汉骑兵“赶鸭子”似的,赶往西方。《大英百科全书》中这样写道:“让人无比惊讶的是,人类骑兵时代的实现居然是因为马镫的发明。”
历史上北方蛮族南侵,并可以征服高等文明,是因为北方民族拥有大量战马,始终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和节奏感[18]。无论是被西方人称为“上帝之鞭”的阿提拉,还是后来建立欧亚军事帝国的“成吉思汗”,都是利用战马的机动性打败对手的。到了唐代,战马背上既有鞍,又有蹬,唐三彩中的三彩马,李世民的坐骑“昭陵六骏”,就装备齐全。8世纪时,马镫随着“上帝之鞭”阿提拉传入欧洲,欧洲人给它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Chinese Boots(“中国靴子”),欧洲也因此进入了“骑士时代”和封建社会。
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高度赞誉马镫:“几乎没有什么发明像马镫这么简单,但也几乎没有什么发明像马镫这样对历史有如此的催化作用。”[19]同样,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中也给马镫极高评价:“只有极少数的发明像马镫这样简单,但却在历史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响。就像中国的火药在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帮助摧毁了欧洲封建主义一样,中国的马镫在最初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
中国人是实用主义者,从古至今都如此。比如说“羊”,他们觉得羊长大了就很美,所以,古人释义:“羊大为美”。羊长大了,就可以吃上鲜美的涮羊肉、烤串儿,当然“美”啦!鸡、狗也一样,公鸡能打鸣,母鸡会下蛋;狗在家能看家护院,外出还能打猎作战。鉴于他们的实用性,所以古人对他们须臾不忘,即便“一人得道”,也要“鸡犬升天”,带走追随自己的禽兽。另外,“舌尖上的中国”,中国人作为吃货民族,最敢吃,也是最会吃的。六畜除了实用功能外,还是肉食的重要补充。
参考文献
向上滑动阅览
[1]《周书》:“神农之时,田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然后五谷始兴,可代果实。”
[2]《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育人民。”《贾谊新书》:“神农尝百草之实,教人食谷。”
[3]《论语·微子》:“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
[4]晁错《论贵粟疏》:“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5]赵丽杰:《试论高粱传入中国的时间、路径及初步推广》,《中国农史》,2019年第1期。
[6]《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7]《汉书·食货志》:“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
[8]《晋书·食货志》:“昔汉遣轻车使者氾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
[9]《淮南子·本经训》。
[10]《孔丛子•陈士义》:“猗顿,鲁之穷士也,耕则常饥,桑则常寒,闻陶朱公富,往而问术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当畜五牸,於是乃适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滋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以兴富於猗氏,故曰猗顿。”
[11]《史记·货殖列传》:“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12]《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以屠狗为事,与高祖俱隐。”
[13]《韩非子·五蠹》:“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
[14]徐中舒:《耒耜考》,见《农业考古》1983年01期。
[15]张荫麟:《中国史纲》,中华书局,2016年版。
[16]《尽地力之教》:“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
[17]熊培云著:《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
[18]《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十六)·论御虏疏》:“虏所以轻侮中国者,惟恃弓马之强而已。”
[19]转引杜君立著:《历史的细节:马镫、轮子和机器如何重构中国与世界》,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